【经典解读】胡岳岷 付文军:异化劳动的出场逻辑与理论反思——从《巴黎手稿》到《资本论》
来源: 时间:2022-06-29 13:30【字号:大 中 小】
《巴黎手稿》堪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先河之作”,而异化劳动理论又是这一力作的核心概念。自1932年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关于这部手稿是否为马克思的成熟之作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就是马克思是否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他的异化劳动思想。我们认为,异化劳动不仅与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等一同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哲学批判的核心主题,也是马克思借以展开其批判图景的依据。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从多维视角出发把‘劳动’理解为‘异化劳动’,此即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关键所在”[1]。因此,对异化劳动的理论阐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路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异化理论不仅体现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架构中,而且贯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始终,更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升华。本文试图沿着从《巴黎手稿》到《资本论》的演进线索,对异化劳动理论做一个理论反思。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是贯穿于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一根红线。在劳动发展史上,劳动也先后历经了“对象化→异化→对象化”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作为劳动的两种样态,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变迁。在对劳动的科学考察中,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状况的切身体察中,马克思实现了对劳动概念的理性认知。对象化,即“本质在自我发展过程中成为异于自身的对象的过程”[2]。自在自然作为人类持存的基本构件,并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要求,而需要人们按照“为我之物”的要求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转化为人化自然,为我所用。这一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变,即人类对象化劳动力量的彰显。正是通过这一对象化的活动,我们自身的能力才得以彰显,才能将周遭世界赋予人化的形式。唯在此时,我们方能感知到自身以及周围自然界存在的意义。可见,劳动的产品即固定于某一对象中的物化[3]劳动,此即对象化劳动(或者说是劳动的对象化)。一言以蔽之,劳动的实现过程即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世界的变换并不带有侵占和剥夺等敌对性质。这样的转换,“是一种自觉的、互利的,甚至等价的生产、社交活动”[4]。对象化劳动是劳动的肯定方面,是劳动积极本质的表征,“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表征,是属于世界的存在方式”[5]。异化,“即有转化的活动、过程、状态的情景,更有转化而来的性质的变化,有明显的丧失含义;即转化后处于外在的、孤立的、对立的性质和地位,即相离相违;而且从主观目的来说是相悖的,不曾预料到的等等”[6]。简言之,异化劳动是对劳动转化为——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和结果上——反制自身的活动(具有一种逻辑上的主体自反性)。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分工的不断细化,劳动原来所拥有的力量会逐渐变质,继而僭取“一种与人及其愿望和计划相分离的存在”[7]。在这种劳动中,“对象化”既表现为被对象所奴役,又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过程;占有则相应地表现为外化(或者异化)[8]。异化劳动是劳动的否定方面,是劳动否定本质的表征。“当马克思最终坚决站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从原则上排除了同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前景作任何妥协的可能”[9]时,异化劳动问题就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呈现在马克思面前了,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课题。异化劳动并非马克思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它的出场既同马克思批判思路的转变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又与当时普遍“强制”的社会现实相契合。《巴黎手稿》是马克思在勤奋研习国民经济学家思想的基础上,哲学思潮与经济学思潮碰撞而溅出的火花。在现实斗争的旋涡中,马克思因难于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而苦恼不堪。为了不“作践自己”[10],他选择退出《莱茵报》,开始挖潜“难事”及现实中工人受苦受难背后的根源——私有财产所有制。通过实践和反思,马克思开始批判性地省思前人的理论(主要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并对黑格尔法哲学作了“主宾颠倒”的首次尝试。他摒弃从“国家”和“法”之中去寻找解开人类历史之谜锁钥的做法,而诉诸“市民社会”。简而言之,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法”的观念和“国家”的形式植根于“市民社会”(物质生产)中,故而对于“市民社会”的批驳就很有必要了。同时,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从另一条道路横空出世,和马克思实现了思想上的胜利“会师”。受恩格斯的启发,加之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自觉要求,使他觉得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须成为现实。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路径就表现为:政治批判(国家和法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在马克思的思想之旅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并非其论说的终点,在研习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他又开启了一条更具体和更有力度的批判,即对劳动的批判。这使马克思的批判思路更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哲学—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批判”。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异化劳动并非自然地呈现于世人面前,而是透过深入地亲身体味和理论挖掘,才以被动的形态彰显出来的。在马克思的批判语境中,其视野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继而落脚到劳动之上。这一转向的背后,关键之点便在于私有财产所有制,正是对其理论疑难的深刻剖析,方才有对异化劳动的明晰表述。马克思立基于“劳动和资本的分离”这一国民经济学的“前提”,采用国民经济学家的“语言”和“规律”,来对私有财产所有制下的劳动进行深入分析。正因为“劳资”的分离,工人被降格为商品,并且是最为低贱的商品;工人的清贫和困苦同其所创造的产品之间成反比例关系。因此,才有了没有财产的阶级(无产阶级)和有财产的阶级(资本家)的区分,才有了前者饱受压榨而后者尽享富贵的局面,才有了劳动反制自身的“异化”表征。这样,劳动的发展历程也就以“劳动→异化劳动→……→劳动”的形式,较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正是沿着“哲学—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批判”的批判路线和“劳动→异化劳动→……→劳动”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异化劳动就水到渠成地登场了。正是基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细致研究和深刻批判,“异化劳动”才被马克思作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提炼出来并嵌入其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之中,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在场存在”,从而使“异化劳动”学说,成为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经济批判的主要内容。我们知道,任何论说要有意义,必须言之有物,即要形成对现实的观照。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时代的呼声的现实表达。异化劳动的出场势必要牵涉它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社会强制作为私有财产所有制社会中的一个普遍存在,诱发劳动变质为“异化劳动”的现实土壤。非常明确的是,在私有财产所有制产生之前,人们肯定不知道“异化”为何物。人们囿于狭小的圈子里而自给自足、自得其乐。诚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野人只有在“洞穴”中才没有陌生之感,鱼只有在水中才会觉得是自在的。[11]他们自得其乐地活于洞中的状况与原始而低级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此时,未有人身依附(强制),这一其乐融融的状况在私有财产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强制)之下,几乎是一个不可能事件。在私有社会中,劳动者囿于严格的人身依附(强制)之中,劳动者之于自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乌有之乡,对自由亦只能持仰望姿态;在资本逻辑的制约之中,面对劳而不获和获而不劳的两个极端,唯有望洋兴叹。人身依附(强制)自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出现之日便开始发挥作用。从严格意义上讲,在这种强制之下,劳动者并非具有自由劳动能力(这一自由程度如何暂且不论)之人。他们至多只能以“有产者”的财货(奴隶、农民和雇佣工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一定的阶级)的身份见世,故其所劳和所得,顺理成章地直接隶属于他的“主人”。历史和实践经验证明,作为“财货”的劳动者生产愈多,遭受的剥削也就越重;其创造的商品愈多,他自身也就愈廉价——这可谓异化劳动苗头的初步展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开始作为社会原则逐渐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时候,社会财富因资本家的“勤劳”而集中其手。理论上,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物应尽数归劳动者所有,这是合乎逻辑的理论表达;然而,在现实中,作为财富创造者的工人却只获得没有就不行——“同‘普通人’即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12]——的一点微薄的“工资”。理论表达和现实状况之间的两歧,使劳动由人的积极本质裂变为否定自己的强制劳动。具体而言,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自身所拥有的体力和智力得不到自由发挥,劳动活动亦不能使其感到自在和畅快,一切都是被迫为之,劳动的真实意义纷纷走向其反面,劳动的积极本质也逐渐裂变。随着批判的不断深入(即“哲学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批判”),加之普遍“强制”的存在,劳动本质发生裂变(即“积极本质→否定本质”),异化劳动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具备了出场的条件。劳动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与人类社会持存的基础,一部人类史即一部劳动史。可以说,劳动是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锁钥。在私有社会中,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却被迫异化了。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缜密理论思考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切身体会,完整地论述了劳动的异化处境。通过对马克思的两大经典文本《巴黎手稿》和《资本论》的研读,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异化”一词在《巴黎手稿》中出现了107次(指字面,不是含义,下同),“异化劳动”一词出现了23次,“自我异化”一词出现了21次。[13]结合《巴黎手稿》的文本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异化劳动是《巴黎手稿》的核心命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最为犀利的武器。这一情况在《资本论》中似乎发生了翻转。在《资本论》中,“异化”一词仅仅出现了18次,“异化劳动”的出现次数竟然为0。那么,我们可否由此断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然抛离了“异化劳动”批判的逻辑主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一,异化与异化劳动是马克思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始端,同时也是贯穿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思想进路始终的一个核心概念。毫无疑问,虽然异化劳动在《资本论》中出现的次数为0,但并不代表马克思无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异化问题。虽然马克思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思想境界已有很大变化,但并不代表马克思抛离了早期建构的异化劳动理论。那种认为异化概念只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不成熟的表现,并在成熟时期的著述中(特别是在《资本论》)已然抛弃这一观点的说法是没有透彻理解马克思著作的臆断。“在马克思一生的不同阶段,他对异化内涵的理解确实有所变化,但‘异化’始终是他思考社会、透视人性的重要方式和领域之一,即使我们还不能像用‘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词汇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用‘异化’来概括马克思的思想,但可以肯定,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视阈中,异化思想始终是不可或缺的。”[14]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产物,与私有制度相倚相生。如此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势必要有对异化劳动的考察和研究。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细致的理论省察,断言劳动即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15]。从《巴黎手稿》的逻辑理路来看,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可谓大工业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亦是对异化劳动理论展开认识的理论成果。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一切财富都是工业之财、劳动之富。作为“完成时态”的劳动,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被包含在工业的“主体本质”之中,继而“喧宾夺主”,使工业的“主体本质”换化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这一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了贯彻和发展。可以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拜物教”和“剩余价值”等范畴的批判性分析并未抛离早期异化劳动的分析旨向,而是将其进一步具体化了。就拜物教而言,它是将我们常见之“物”(如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等)视为神灵一般供奉、崇拜,并倾毕生之力去攫取这些“物”。这些“物”成了醉人的尤物,并同时造就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以其为目的。殊不知,这些“物”还不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带有“属人”的标记。当局者迷,拜物教徒被这些“物”遮蔽了双眼,看不到这些“物”中所蕴含着的社会关系维度。继而,这些由人所造出的“物”制约着人们的一切行动和思想。可以说,拜物教也是一种异化现象,只不过它所映现的不是我们表面所见的“物物关系”,“而是物物掩盖下的社会关系”[16]。可见,拜物教也是一种异化现象,人的丰富性维度就此丧失。就剩余价值而言,它是由工人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也是资本家所有活动的驱动力所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资本主义生产的完整画卷: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资本,并在劳动力商品市场上购得劳动力(准确地说是劳动力的使用权),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不间断地榨取由工人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将这部分无偿所得的部分转化为更多更大的资本,继而又购买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如此往复,资本犹如“滚雪球”般地扩大了。关于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指明了它是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的劳动创造。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剩余劳动乃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所在,也是资本得以积累扩大的源泉。在对工人剩余劳动无止境的压榨和盘剥中,资本家得以作威作福,而工人(劳动者)却处于受苦受难的境地。可见,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外就应该获得更多自由时间来全面发展自身,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得以缩短,是为了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创造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这样的劳动也是异化了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始终的一个现象。由此,完全可以说,只要马克思还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为考察对象,就必须要展开对异化的分析;只要马克思还要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必须要将异化劳动理论升华为剩余价值学说。其二,在《资本论》中,劳动异化问题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理论构件。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问题”。就劳动本身而言,马克思直言不讳,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本身”[17],劳动作为人类世界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18],随即表现为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必须指出的是,劳动本身彰显着人之为人的力量,所论及的物质世界的变换过程也是丝毫不带有侵占和剥夺等敌对性质的。然而,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作为人的力量这一能力逐渐消逝,并逐渐变为压抑人、困扰人和剥夺人的一种存在。就劳动过程而言,它是资本家对劳动力这一商品的消费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人的各项活动都在资本家的密切监督下完成。因为资本家“唯一在乎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19],劳动过程就是其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就劳动结果而言,“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20]。简言之,工人辛苦劳动创造的产品并不为自己所有,而为资本家所占。这和《巴黎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何其相似。可以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未直接使用“异化劳动”的字眼来表达劳动异化的事实,但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于劳动异化现状的关注。另一方面,马克思指认了资本逻辑宰制下的异化劳动及其相关问题。异化劳动得以产生是源于私有制,是《巴黎手稿》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其模构为资本的逻辑,从而实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华丽转身。这样讲的依据何在?第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区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活劳动”和“死劳动”,前者是工人,后者是资本。在这里,马克思将“资本”引入劳动异化理论之中,并使之成为内生变量,将劳动资本化,他们之间发生了主客颠倒,即资本对劳动的异化。我们知道,人是主体,本应成为资本这一客体的主宰。具体言之,活劳动具有主观能动性,因而必然要掌控死劳动——资本。然而,这一逻辑顺序却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之下发生了颠倒。劳动过程中的资本,是活劳动的支配者,而与工人相对。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死劳动,只剩下了一种生活的本能——“增殖自身”和“创造剩余价值”,以自身的不变部分(生产资料)尽情地“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21]。这是资本家的经典形象——吸血鬼和寄生虫,以活劳动为宿主,以控制和吮吸活劳动来维持其生命体征。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一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22]。可以说,这一倒置,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23]颠倒。现在,我们采用倒叙法回到《巴黎手稿》中还原异化劳动。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确认了劳动产品丝毫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而成为与劳动相对的异己之物。然而,此时的马克思只提到了劳动及其产品的“异己力量”。至少在这个阶段马克思还没有把隐藏在异化劳动表象背后的秘密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却撕下了它的神秘外衣,让它赤裸裸地站在了世人面前。第二,资本主义诸多的社会经济范畴都制约着劳动者及其活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其反思对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程式。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社会经济范畴——商品、货币和机器等等——都是其批判性考察的对象。就商品而言,它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24],是劳动者劳动的创造物,却不为劳动者所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商品的生产。劳动者是商品的生产者,理应成为商品的所有者。但在现实中却截然不同,劳动者拥有的仅仅是自身所具备的“劳动力”,对于其他创造物,他们或没有或仅享有极少的占有权。事情还并非如此简单,商品不仅不被劳动者完全所有,还以劳动产品本身所固有的“物的性质”掩盖着劳动者本身所有的社会性质。简言之,商品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物关系”的虚幻形式,而使人们在其面前陷于迷失的境地,并引导和控制着劳动者本人。就货币而言,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是便利交换的创造物。货币应是劳动者经济交往活动的结果,是同商品一样应是受劳动者支配的东西,但众多拜金主义的社会现象是对这一理想状态的有力驳斥。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货币不仅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之职能,不仅是确保流通顺利进行的等价之物,还是社会人争相占有的存在物。对货币的觊觎使人们不断调整经济活动方案,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丧心病狂地榨取工人的血与汗。正是这种“榨取”,使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货币貌似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反制着劳动者。就机器而言,它是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效率的关键。然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者却被机器所左右,成为它的附属物。由于机器的广泛采用,劳动的“任何独立的性质”随即消失,劳动者被视为“附属物”与“死的机构”并列而“服侍机器”[25]。同时,机器劳动不仅对劳动者的神经系统有着极大的损害,还对肌肉系统有着莫大的伤害,甚至将与劳动者相关的一切身体和精神方面的“自由活动”[26]都剥夺殆尽。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机器这个现代社会的“怪物”作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体系中又一个变量站了出来。因此,我们不要以为《资本论》中未直接出现“异化劳动”四个字就武断地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抛弃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直言,以《资本论》为题的这部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为批判研究对象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撕下了自己温情脉脉的面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关系都是商品关系、金钱关系,都是异化劳动关系。只要我们认真研读《资本论》,就会发现这部鸿篇巨制通篇充盈着批判异化劳动的思想光芒。《资本论》是马克思将其异化劳动理论在一个更大更高更广阔实验场里做了一次更加伟大的尝试。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资本论》中异化劳动理论得到了升华,其思想光芒反而更加璀璨地绽放了。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就社会中工人的现实境遇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马克思反思的逻辑表现为依次递进的四个层次。1.异化劳动的归属问题:异化劳动到底是否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从前文可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是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核心议题的。在《巴黎手稿》中,这一主题的出场是基于对“当前的经济事实”的考察,而非经验臆断。在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凡涉及“资本主义”之处,多会(直接的或间接的)有异化劳动的身影。然而,我们真的可以由此笃定异化劳动独存于资本主义社会吗?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并未给予明确的回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异化”这一术语适合于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工人和资本家关系的诸多论述:人为自身的创造物所反制,人们之间的关系都变了质。马克思退回书斋,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观察和对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反思后,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私有财产;劳动、资本、土地的分离;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离等等)出发,揭露了工人持续贫困的现状及其背后的根源——劳动异化,即工人被其自身所创造的物所役使,自身的行为或结果与之疏离。异化劳动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大理论主题,其存在形式与私有财产息息相关。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异化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通观《巴黎手稿》和《资本论》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文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阐发,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这一语境下完成的。无论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梳理工作,还是对劳动异化状态的剖析,都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有制和分工密切相连。随着私有制和分工的发展,劳动失去了彰显人之本质力量的这一特质,劳动及其后果僭取了一种同人的本真相分离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化劳动这一存在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休戚与共。但是,就此断言异化劳动专属于资本主义是否有充足理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第一,马克思虽未明确交代异化劳动的归属问题,但也未给异化劳动印上独属于资本主义的“标签”。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源于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扬弃,在后者看来,人的历史即是一部人类异化史。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认为异化是基于这一事实:“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相疏远,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地是的那个样子”[27]。换言之,“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他应当成为他可能成为的那个样子”[28]。从异化劳动的发展过程来说,它是劳动的一种暂时存在状态。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分别作为劳动的“积极本质”和“否定本质”,“对象化→异化→对象化”的演变过程,构成了劳动的发展史。同时,自由自觉活动的不断异延与裂变,使劳动发生了异化。这就表明异化劳动是历史的产物,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因此,要将异化问题置于历史视域中进行慎重的考察。若要继续追问劳动在何时发生异化?马克思并未给予明确的答复。为此,可举一“反例”来确证异化劳动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封建土地的占有为例作了说明。“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农奴是土地的附属物。同样,长子继承权享有者,即长子,也属于土地……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29]。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现象并不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才产生的,早在封建时代便已存在。第二,异化劳动并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其存在、发展和消亡都和私有财产密切相关。马克思专辟“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内容来阐释二者间的关联,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通过全面而准确地把握“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明了异化劳动的肇因在于私产和分工,并随着私有制和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而得到了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得以异化,并非一时之功。换言之,劳动异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决然不会凭空生成,其存在和发展必然有一过程。唯当人开始脱离原始自然状态而逐渐迈入私有社会之日起,才会自觉不自觉地处在异化过程中。而在私有财产还未生成的日子里,异化由于缺乏持存的基础而不会产生;在私有财产被彻底废除的未来,异化也会由于没有“宿主”的供养而销声匿迹。在这两种状态之间,也即私有制存在的社会里,劳动将不可避免地陷于异化的困境。在马克思思想深处,一直认定劳动异化是在全部私有制历史中存在的,而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劳动的异化程度达至巅峰,工人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也是最为严重的。同样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论及分工之时,就已然确证了分工(自发的分工,而不是自愿的分工)就是异化的一种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内,分工犹如一个“剥离器”,使一切社会存在物——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城市和乡村——裂变开来。在《资本论》中,尽管较少提到“异化”一词,但它依旧以“形变”——“物化、拜物教”和“物役”——的形式存在。后者作为异化的变形,也是对现今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新表述和再归纳。可以说,异化劳动同资本主义是相生相倚地存在,但并非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因而,将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关联起来,有一定的理由,但并不充分。总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异化劳动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不是自然生成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异化劳动的存在与私有财产的生成同步,其发展和消亡亦与之同步;异化劳动是历史的产物,势必不会专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它共属于私有社会。2.异化劳动的存在问题:异化劳动到底是否是一个纯粹否定性存在异化劳动作为资本大工业生产中的一种确定性存在,是工人悲惨境遇的始作俑者。因此,对于这种劳动必须要给予否定和鞭挞。然而,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必要环节的异化劳动,它仅是一种否定性存在吗?马克思虽未明确回复,但问题的设计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异化劳动是一种否定性存在,理应招致严厉批判,这毋庸置疑。异化劳动作为资本大工业时代普遍的社会现实,作为对人之生存境遇的一种体验方式,是私有社会的“痼疾”。马克思剖析了三种可能出现的社会状态及与之对应的工人处境:当社会的财富处于衰落之时,工人遭受的苦痛是最大的,“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30];当社会的财富处于增势之时,“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31];当社会的财富达到巅峰之时,工人所得的工资和利润都处于极低的状态,工人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更为严重的是将导致部分工人丧失工作而死亡。马克思总结道:在私有社会中,“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32]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是异己的,是受到排斥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类生活和个人生活都是异化的,它将“类生活”贬低为维持个人生计(牲畜般存在)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状况被改写,对自然的无节制攫取换来的将是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环境危机反制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状况被打破,人与人的关系被严重物化,物成为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大标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也十分尴尬——人将不人,人在私有条件下变成了“异己”的、“非人”的“对象”,人的现实化也即“异己的现实”[33]。简言之,异化的劳动中断了人们“自我实现”(通过劳动确证自身本质)的潜能。作为一个心怀大众的学者,马克思就不可能只停留于对工人惨况的揭示而不去探究惨境背后的根源,也不可能止步于阐明惨境背后的根源而不去找寻化解这一悲惨境遇的良方。通过分析发现,异化劳动既是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也是阻挠人占有自己真正本质的障碍。因此,异化劳动作为一种否定性存在,马克思就不得不站在道德立场对其进行无情的挞伐。“批判”是马克思的本真精神,也是马克思“为学”的关键。异化劳动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应对其辩证审视。异化劳动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它对于人们生存状况的揭示和反思,为理论家和社会实践家们找到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对症下药”的依据。“马克思将他的异化观阐述为一种内容广泛的观念,其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中的诸多罪恶和非理性,并将二者联系起来。”[34]从这个意义上说,异化劳动又不是一个纯粹否定性的概念。当然,异化劳动固有其“恶”,但“恶”又是必要的。一方面,异化劳动作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体验方式,控诉了私有社会中的阴暗面。异化劳动的发现,把准了国民经济学这一矛盾躯体的脉搏——表面承认人,实则是对人的彻底否定,人本身不再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而是相反;异化劳动的“出场”也全面地印证了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35],是一切财富之源,劳动所有权本应属于其真正主体,但工人所得却“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36]。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理论分析,私有社会中的一切弊病都被揭示出来,人的异化了的生存境遇得到了确证,私有社会中一系列“二律背反”[37]得以阐明……另一方面,异化劳动作为一种理论建构,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未来路向。通过以劳动的人为中心,考察同时代人的生存状况,形成了对粗陋和平均共产主义的驳斥。前者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因而它只是“想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38];后者并未了解私有财产主体的积极本质,也难称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对异化劳动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路向——扬弃私有财产的社会(共产主义)。在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的社会里,人才能真正实现向自身的复归,才能实现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一言以蔽之,若不通过异化劳动的理论反思,就不可能揭穿对抗性社会中全部人的存在的矛盾,就不可能披露资本主义非人道的性质,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论说,这正是其积极意义所在。作为劳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作为劳动的一种形式,异化劳动绝不会是劳动发展的最后状况,因而它是一定历史时代必经的一个现象,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前提。异化劳动是人类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和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正是对异化劳动贬低一切价值、与各个领域格格不入现状的认知,才能打开人们的视野,厘清社会矛盾现状,寻求克服劳动异化的途径,进而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阐明。因此,对于异化劳动理论的评判不能仅停留于道德范围内,应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3.异化劳动的根源问题:异化劳动到底是不是单源于私有制异化劳动在私有社会中蔓延开来,并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达到顶峰。马克思客观地揭示了异化劳动“这一事实”,而问题在于,“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39]对这两大追问的回应,马克思将视线转向了私有财产,并认定“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40]。那么,异化劳动的问世,仅仅是源于私有财产的吗?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家那里找到了私有财产运动结果——异化劳动。同时,马克思又确证了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必然后果。[41]由此来看,私有财产既被视为异化劳动的诱因,又被视为异化劳动的结果。这有着明显的自相矛盾,像马克思这般机敏的理论家是否犯了“低级错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此之后”和“由此之故”的单向运行,并非完全是马克思因果逻辑所包含的内容,其间还应蕴含因果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马克思关注的重点在于二者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犹如一对孪生姊妹,二者间有着须臾不离的关系。私有财产来源之谜的侦破有赖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而从对私有社会现象的透彻分析到对其本质的切身体会,又必然落脚于异化劳动,这是两条并行不悖的理论分析入径。由是观之,“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在更加确切的意义上讲,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后果”。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胡乱说辞,也并非我们所认为的循环论证。[42]这一矛盾如同“神”与理性的“迷误”之间的关系一样,神起先并非人类陷入“理智迷误”的原因,而只是其结果而已。可见,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其间的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这一后果又反过来会改变劳动的性质,使劳动发生异化。其实,异化劳动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这个谜充满着神奇的魅力,诱致着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无穷的神思和想象力。从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分析中,不易找到劳动异化的根源。劳动是人借助于一定的工具同自然发生关系(主体—媒介—客体),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活动,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劳动即主体按照“为我之物”的要求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和占有过程。人既是劳动创造的主体,又是劳动成果享受的主体,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在劳动创造过程中暴露无遗。按照这一基本思路,劳动者是造成劳动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内因”。因此可以断定,异化劳动的根源不应在人之外,而应在人自身中去寻找,即应在人自身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处于社会中的人要表现自身,要确证自身的存在,“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43]。在对劳动异化的分析中,劳动活动及其所得,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之物,“只能是人自身”[44]。唯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45],这是私有财产和财富分配所无法达成的,也是神和自然界无能为力的。因此,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私有财产所有制是劳动异化的一大条件,然而,并非唯一诱发性因素。异化劳动既不单源于私有财产所有制,也不单源于人自身,而是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4.异化劳动的扬弃问题:异化劳动的克服到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异化劳动是劳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是历史之产物。通过对人类劳动发展历史的考究,确证了劳动发展阶段的否定之否定,即“劳动——异化劳动——劳动”。异化劳动只是劳动发展史上的一个“过客”,有其产生,必有其灭亡的过程。然而,对于迟早必将消逝的异化劳动,其消亡——积极扬弃——的过程是否能一蹴而就呢?马克思描绘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时代”——共产主义,并在此之中找到了扬弃异化劳动的标识和条件,从而对此问题作了有效的回应。诚然,异化劳动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具有阶段性和历史性。因此,异化劳动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必须遵循“发生→发展→灭亡”的一般新陈代谢规律。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巅峰,钳制着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攫取着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管控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其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妨碍人们对公平和正义的正常追求之时,将不可避免地趋于灭亡。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人类劳动向更高层面的复归,这是生产力和人类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至顶点(最高阶段),接下来就必会灭亡,这也是不可抗拒的劳动新陈代谢的规律。这在《巴黎手稿》及其之后的文本中也是得到马克思首肯的。一句话,异化劳动的扬弃,是历史之必然。当然,作为一位具有“普罗米修斯”情结的学者,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深入剖析,其目的并不在于断言异化劳动的扬弃不可避免,而在于探明异化劳动的克服之道。唯此,才对异化劳动的问题有一完整“交代”。马克思预感到了积极扬弃异化劳动之路并非坦途,并有意或无意地预言这将是一个漫长而逐渐逼近的过程。马克思在清晰把握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两者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将异化劳动的克服归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与其他私有社会不同,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私有社会的积极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解放,此时的人才是具有丰富、全面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一种“总体的人”对自己的本质进行全面而真正的占有。而由历史带来的“共产主义行动”,即“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46]。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找到了解开人类“历史之谜”——人类社会从何处来,又将向何处而去的钥匙,另一方面却把“解锁”的具体操作过程“悬置”起来。作为一个手稿,其意义在于为异化劳动的克服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强调需要通过实践的方式,借助于实践的力量,才能实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47]。而富有浪漫主义情调地高扬“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48],则有赖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物质世界的充裕和普遍交往的实现等等条件。显然,在《巴黎手稿》中,不仅指明了克服异化劳动的方向——共产主义,还指明了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一个极漫长的过程,人类发展的每一步都只是向这一目标的逼近。简言之,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兼具必然性和长期性于一身。《巴黎手稿》和《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史上的典范之作,其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不容小觑。《巴黎手稿》是马克思转入经济学研究后的开先河力作,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文稿透过对异化劳动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和系统性探讨,实现了私有制和市民社会等相关核心概念的勾连,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支点;它作为对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精准刻画,揭开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模态——不仅揭示了私有条件下劳动的异延和裂变形式,而且揭示了当时工人真实的生存境遇,特别是其存在之难,继而探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资本论》则是凝聚马克思毕生心血的集大成之作。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种种异化关系的考察,揭开了资本主义诸多社会现象的神秘面纱,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在《资本论》中,异化劳动理论被拓展为剩余价值理论,那种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抛弃了异化概念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可以说,异化劳动理论并没有在半程中消失,而是从《巴黎手稿》出发,跟随马克思,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上攀登,在《资本论》中华丽转身,升华为剩余价值学说,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先河之作的《巴黎手稿》和巅峰之作的《资本论》,犹如两座不朽的丰碑,正高高耸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史的高峰之上。在这里我们能够告诉那些否定者的是:“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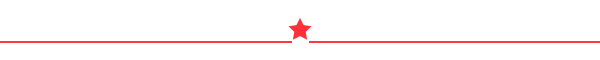
[1]Bertell Ollman,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ina Capitalist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170.[2]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8页。[3]物化,从广义上来说,指的是主体活动凝结成物质成果的过程,也即主体属性客体化的过程;从狭义方面而言,则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人的关系表现为物的特征,即生动的主体变为凝固、僵化的客体的过程。前者是物化概念的积极含义,后者则是其消极含义。[4]韩学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5页。[5]邹诗鹏:《对象化、非对象化与人的本质活动——兼论美感生成的生存论根据》,《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6]韩学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5页。[7]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60页。[8]在《巴黎手稿》的语境中,异化和外化通常是并用的,并不作特别的区分。然而,并不表示这二者“同一”。外化通常指的是人本质力量之彰显,至于对象化(除了显示人之本质力量外,还强调行为结果,即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的实现,物化为对象或者产品)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外在化这一行为本身。异化则主要强调行为后果的敌对性质,反过来残害主体自身,制约主体自身的发展等。[9]尤·尼·达维多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问题》,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3页。[10]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期间,因当时的“伪善”“愚昧”和“粗暴的专断”(如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令他感到厌恶而辞职。他将在这样氛围下工作的人视为“自己作践自己”之人。[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8页。[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13]韩学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46页。[14]刘秀萍:《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16]付文军:《资本、资本逻辑与资本拜物教——兼论〈资本论〉研究的逻辑主线》,《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7-208页。[19]付文军:《资本、资本逻辑与资本拜物教——兼论〈资本论〉研究的逻辑主线》,《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9页。[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3-294页。[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0页。[24]胡岳岷:《〈资本论〉的中介方法论》,《江汉论坛》1997年第7期。[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6页。[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6-487页。[27]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页。[28]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页。[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1页。[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2-303页。[34]史蒂文·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袁聚录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7页。[35]尤·尼·达维多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问题》,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3页。[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37]马克思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现实社会的切身体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一系列悖论,如劳动致富和劳动者的贫困、工作日的控制和延长、减少人数和增加产量、节约和浪费、价值的增值和丧失等等之间存在悖反。[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7页。[42]关于马克思此中的“循环论证”问题,国内和国外学界都作了回应。日本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正面回应,大井正、梅本克己、广松涉、服部文男、望月清司、山之内靖等等都从正面回应和解决了所谓的“aporia”问题。国内学界率先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陈先达先生,他区分了“作为与私有制不可分的异化劳动”和“产生私有制的异化劳动”,后者先于私有制而存在(参见《陈先达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魏小萍先生也从“外化劳动”(dieentuerteArbeit)和“异化劳动”(dieentfremdeteArbeit)以及“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区分中解决“异化劳动理论不是循环论证”的问题(参见魏小萍:《探求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7页);王峰明先生认为马克思着眼于“现实”的关系,阐明了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之本质和规律。或言之,异化劳动之于私有财产具有本质和规律意义上的“优先性”和“决定性”。借此,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在马克思处并非循环论证,而是对二者相互作用所作的阐释(参见王峰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试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个理论难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韩立新先生则认为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分别使用了两种异化劳动——“作为对象化活动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Ⅰ,人把自身的体力与脑力注入到自然对象中,使对象成为人可消费的劳动产品,但这一活动毕竟还含有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于他者中,此即异化——Entfremdung——的本义)和“属于他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Ⅱ,劳动者的劳动及其成果不属于自己,而归他人,这也是异化——alienation——的本义)。同时,马克思还使用了两种私人所有——“基于自己劳动基础上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Ⅰ,劳动者所有自己的劳动条件和成果,并在意识中和市民法中,确证所有物属于自身,而不属于他人,此即私人层面上的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Ⅱ,建立于自己劳动基础上的私人所有剥夺的基础上,实质就是资本本身)。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逻辑理路即“异化劳动Ⅰ→私人所有Ⅰ→异化劳动Ⅱ→私人所有Ⅱ”,由此,“循环论证”之谜得以破解(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2-211页)。[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5页。[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7页。[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文献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