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韩立新:“物”的胜利——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货币章》为中心
来源: 时间:2022-07-28 13:30【字号:大 中 小】
人,而非人的创造物,才是世界的主人,这是自启蒙以来确立起来的思想常识,也是近代哲学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近代世界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人的一种特殊对象物,即交换价值、货币和资本。如果把人与物的关系比作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话,恰恰是在人的主体地位被凸显、人的主体性最为发达的近代,物却取得了对人的全面胜利,人沦落为物的客体。更令人意外的是,对这一惊人的结论,马克思并非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而是通过严格的理论证明给出的。关于这一物对人的胜利过程,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穆勒评注》中就曾给出过初步说明,后来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作出了全面的阐述。这主要跟人类历史进入到它的第二大阶段即近代社会,以及近代社会又以交换价值、货币和资本为主体有关。我们知道,《大纲》主要包括《货币章》和《资本章》,两章结构分别对应近代社会的两个层次:简单流通和资本主义生产,或者按照笔者的分法,即“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和“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所谓市民社会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平等的市民自由地交换其商品的社会组织。在这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物是交换价值和货币。从内容上看,它与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相似。所谓资产阶级社会则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在这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物是资本,社会也因此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两大阶级。《货币章》的理论世界是市民社会,《资本章》的理论世界是资产阶级社会。在《货币章》中,物以交换价值或者其最高体现者货币的身份获得了主体地位,而人则“物象化(Versachlichung)”为商品或者货币,转而开始对物的全面依赖;在《资本章》中,作为交换价值的更高次方,资本将包括人在内的世间的一切都变为自己增值的客体性因素,以世界唯一主体的身份将整个世界同化为资本的世界,而人则以活劳动的形式“物化(Verdinglichung)”为资本的客观的生产条件,下降到与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同列的地位。从《货币章》到《资本章》,物呈现出主体性不断上升,人则呈现出主体性不断下降、直至丧失的过程。整个《大纲》所展现的不外乎是人与物的主客颠倒,人的世界被物的世界所取代的过程。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考察《货币章》中物对人的胜利过程。康德曾将世界中的事物分为“人格(Person)”和“物件(Sache)”两类,认为人格因具有自我意识而能成为世界的主体,而物件则因无自我意识而只能是被人格统治的客体。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人为什么是主体,物为什么是客体的标准解释。的确,自我意识的有无对于人通过劳动将自己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与物形成一种主体与客体关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人因此成为决定人与物关系性质的一方。亚里士多德把人视为“形式因”,而把物视为“质料因”,认为形式相对于质料居于主导地位。马克思也认为劳动是“活的、造型之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9页),可以让“客体从属于主体的目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活动的结果和容器”(同上,第481页)。从他们的主张来看,人与物之间只能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一关系的基本理解。笔者把它称作“人与物=主体客体关系模式”。在“人与物=主体客体关系模式”中,物本身不具有“独立性(Un-abh ngigkeit)”,它对人具有“依赖性(Abh ngigkeit)”。按照黑格尔的解释,这是“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黑格尔,2010年,第52页)。也就是说,物不具有像人的意识或者意志那样的目的性,只有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财产,被纳入对人的关系当中时,它才能从死的自然变为活的对象,物的价值和意义要依赖于人的承认。而与物不同,人的价值和意义不依赖于物的承认,其本身具有独立性。在劳动中,人把自己的体力和脑力等本质力量赋予物,直接参与物向人的生成过程;物反过来作为人的作品,就如同一张桌子反映木匠的手艺、一座雕塑表现雕刻家的创作水平一样,是对人的个性及其本质力量的最好证明。在这种关系中,人与物是直接统一的,物即自己的人格本身,物的丧失就等于人格的丧失。笔者把这种关系定义为人格性关系。在这种对物的人格性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人格对人格的关系。人作为一种共同性存在,是必须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人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产品交换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产品交换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无中介的交换,譬如原始共同体或者市民社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换。此时,由于劳动产品本身是人格的代表,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意味着人格之间的相互补充。通过交换,交换双方不仅确认了对方的人格,也确认了自己的人格。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把这种无中介的交换称作“交往(Verkehr)”(参见马克思,第173页),并视其为人的本质。既然无中介,人们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人格之间的相互依赖。故在《大纲》中,马克思把以此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定义为“人格的依赖关系”阶段(Marx,1976/1981,S.9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另一种是有中介的交换,譬如以私有财产、商品、货币等为中介的交换。同上一种形式相比,这种交换必须借助于中介物才能完成,故它是交往的异化形式。它属于人类社会进入市民社会以后才出现的交换形式。之所以会出现有中介的交换形式,是因为生产目的变化。在“人格的依赖关系”下,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人的需要,其目的是人本身。此时人是主体,而物则表现为人的客体。但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建立,生产目的也随之转变为交换价值。关于这一转变过程,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有过详细的说明,即这是由劳动变为“营利劳动”①所致。所谓营利劳动包括两个特点:第一,“营利劳动以及劳动者的产品同劳动者的需要、同他的劳动规定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第二,“通过交换,他的劳动部分地成为收入的来源。这种劳动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了。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的”。(Marx,1981,S.455;参见马克思,第174页)也就是说,营利劳动不以人的直接需要为目的,而是以交换价值或者货币为目的。而货币同具体的使用价值相比毫无用处,因为无论是纸币还是金银,其本身都不像食品等有用物那样,可直接享受或者消费。正因为它对于人的直接需要而言并非必须,故在饿谨等灾难发生时,货币就失去了意义。可是在市民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目的却偏偏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货币。这与古代共同体的情形相反。马克思写道:“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9页)这里的“财富”并不是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而是指交换价值、货币。生产目的的变化将对人与物的人格性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这表现在人的个性将再也无法进入对象物的内部,人格失去了与对象物之间的本质性联系。马克思写道:“每种形式的自然财富,在它被交换价值取代以前,都以个人对于对象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对象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与此相反,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个体,它本身是从流通中来的,它只代表一般,仅仅是社会的结果,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同上,第173-174页)也就是说,在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劳动中,由于人的个性进入对象物之中,物能够直接表现人的个性特征,人格与物之间呈现出一一对应关系,物是对人格特殊性的证明。但是,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劳动中,产品必须表现为货币,而货币又是无个性、无特征的一般物,人格与物之间失去了一一对应关系,生产者在货币中再也无法从中找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交换价值的生产必然排斥物的特殊性,进而也排斥人的个性。从人的一侧来说,由于“他们的个人的特殊性并不进入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59页),人对物的态度自然也就变得“漠不关心”起来。“漠不关心”的德文原文是“gleichgültig”,也可以译成“毫不相干”。马克思在《大纲》中多次使用该词来表示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关系。首先,表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上,“漠不关心”是指生产者对自己的产品本身失去兴趣。既然作为商品的产品早晚要被交换出去,变成交换价值、货币,生产者将不再愿意在产品中投入个人的情感等。现代的企业管理虽然也对商品质量很感兴趣,但那只是希望商品能被更好地交换出去而已,而非对物本身感兴趣。对物而言,既然你只关心怎样把我转让出去,那么我也就不用再在乎你。这样一来,人与物的关系将发生异化:一方面,人与物互不相干,人格失去了与对象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另一方面,物摆脱对人格的依赖,开始从人格性关系中独立出来。其次,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漠不关心”是指生产者对他者的人格失去兴趣。我们知道,人格一词在雅典戏剧中是指面具,隐喻人际关系中的脸面,它反映着人的自然纽带、血统差别等特定的身份规定性。近代以前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换,譬如《白鹿原》中鹿子霖和白孝文之间发生的房屋和土地之间的买卖,其实包含着脸面的内容。但是,在近代市民社会,“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6页)在交换价值的制度下,无论是谁,都被抹去了脸面,都被贴上了交换价值持有者的标签。大家都抛开了自然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都仅仅以交换价值的持有者,而且是等价的交换价值的持有者存在。对交换双方来说,对方究竟是领主还是农奴、是族长还是乡约变得无足轻重,只要他们握有等价物即可。于是,所有人都出现在交换价值的两端。他们以手里的等价物来证明自己与他人的价值相等。因此他们不再是有个性的人,“他们只是作为主体化的交换价值,即作为活的等价物,作为价值相等的人互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58页)他们无脸,无面,彼此陌生,毫不相干;在交换中,为了能让自己的产品卖个好价钱,他们还寄希望对方是陌生人,以便拉下脸来进行交涉;如果不凑巧遇到了熟人或者亲戚朋友,那么也要采取亲兄弟明算账的方式。一句话,生产者要想顺利地完成交换行为,就必须把对方的人格、个性差别置之度外。从这点来看,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关系必然排斥人与人之间的人格性关系。既然人们之间的毫不相干要远胜于彼此之间的亲密无间,于是为了牟取暴利,人们之间就相互欺骗。康德以来“人是目的”的口号在现实中变成了“人是手段”。尽管每个人比任何时候都宣称把他人当作目的,但事实却是把他人当作自己赚钱的手段。马克思曾这样讽刺这一现象:“我同你的社会联系,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我们的相互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在这里,掠夺和欺骗的企图必然是秘而不宣的,因为我们的交换无论从你那方面或从我这方面来说都是利己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私利都力图超过另一个人的私利,所以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设法相互欺骗。”(Marx,1981,S.463;参见马克思,第181页)这一段让人很自然地想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理性章”中的那段名言:“于是在个体性与个体性之间就出现了一种互相欺骗的游戏,每个个体性都自欺也欺人,都欺骗别人也受人欺骗。”(黑格尔,1996年,第276页)的确,明明是在为己,可偏偏说是为他。对这种说法的虚伪性,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无法容忍。既然人格不值得信赖,那么人们就只能将其信赖潜能转移给外部的对象物,即交换价值身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态!其实,既然人格之间以交换价值的形式等值,那么让交换价值来取代人格本来就不再是什么问题。因为在我心目中,唯一能向我提供实效的,不是你的人格,而是你手里的等价物。于是,一个人能否在世界中体面地生活下去,就不再取决于其人格有多么高尚,而是取决于他手里有多少交换价值。结果,最能代表人类共同生活本质的语言也发生了异化:“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马克思,第183页)至此,人格之间的关系将不得不转变为物象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下面将要提到的物象化事态。人类从对自己的对象物漠不关心,进而对他人漠不关心,最后将热情和信任都转移给了物。一旦走到这一步,人离从主体地位上失坠就不远了。而世界是不能没有主体的,一旦主体位置出现空缺,一定会有新的主体来弥补。这一新晋主体,就是作为交换价值最高表现的货币。物要想接替人格成为主体,光靠人的自甘堕落、自暴自弃是不够的,还需要物自身的努力,即必须让自己摆脱对人的依赖,让“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0页)。这一物的上升过程相较于人的下降过程而言,对“人与物=主体客体关系模式”的破坏更为致命。当然,能够上升为主体的物并不是普通之物,而是进入社会关系中的特殊物,即作为交换中介的“中介物(Vermittler)”,譬如金银或者其符号表现纸币等等。它上升为世界的主体分两个环节:首先,它要在商品面前成为上帝;其次,它还要在人类面前成为上帝。我们知道,物最早是作为人的劳动产品出现的。在劳动产品阶段,物还是人的“作品(Werk)”,具有与人格相对应的个别性;在交换价值的制度下,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虽然也具有特殊性,但因其包含交换价值而成为可交换的“物象(Sache)”;商品的进一步抽象化或者普遍化就是货币,即“物象本身(die Sache selbst)”。这里的“作品”、“物象”和“物象本身”三个概念都是黑格尔的用语,他在《精神现象学》“理性章”中曾用它们完成了个体的对象物从个别性上升为普遍性的证明。(参见韩立新,第7章)在《货币章》中,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做法,也分析了“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1页)的过程。但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强调的是下面这一点,即物不仅从个别性上升到普遍性,而且成为“商品中的上帝”(同上,第173页),进而还成为人类世界的主宰。我们先考察一下货币成为商品的上帝环节。在《货币章》中,马克思给货币下了三个定义,即“流通手段”、“价值尺度”、“财富的物质代表”。第一,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它来源于商品,但是高于商品。这意味着它拥有其他特殊商品所不具备的普遍性,是“一种不依赖于商品的,在一种特别的材料、特有的商品上独立化的存在”(同上,第139页)。第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它不仅在某一种商品面前代表交换价值,而且在一切商品面前都代表交换价值。“它是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的每一其他商品的代表”。(同上,第164页)有了它,特殊商品的实现就有了保证;没有它,商品“是否能实现,仍然是偶然的事情”(同上,第172页)。第三,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本来,无论是作为流通手段还是作为价值尺度,货币都还具有手段的性质,但是在变为财富本身之后,“货币由手段变成目的”(同上,第152页)。这与货币的最初使命相悖。随着货币的身份从流通手段、价值尺度转变为财富的物质代表,“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同上,第173页)。本来,货币只是中介,只是商品的从属物,其地位和意义由商品所决定。但是现在,商品只有通过中介才能实现自身,同中介相脱离的商品,失去了自身的价值。譬如,水果、粮食等如果不通过它进入流通,就只能烂在生产者手中。而原本情况正好相反,如果没有水果、粮食在背后支撑,中介毫无价值。中介异化的后果,就是使中介的地位超过位于交换两端的商品,成为主宰商品命运的存在。马克思写道:“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同上,第293页)关于中介的耶稣比喻,早在《穆勒评注》中也出现过。耶稣本来只是连接上帝和人这两个主项之间的中介,他在上帝面前代表人,在普通人面前代表上帝;但是,由于离开耶稣,上帝和人将无法实现自身,结果耶稣竟然成了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神人”。货币的情况与此类似,它一旦被固定为交换的中介,就变为凌驾于所有商品之上的绝对物。(参见马克思,第165页)通过这一比喻,马克思形象地揭示了货币“从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19页)的过程。问题是货币并不满足于只在商品世界中称帝,它还要将自己的统治扩展至人类世界。这就是物上升为主体所需的第二个环节。从货币的角度看,这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商品是生产者的对象物,它是生产者人格异化的结果;生产者的劳动跟商品一样,只有转化为货币才能实现。与商品臣服于货币的逻辑相同,人臣服于货币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与商品不同,人具有自我意识。物要想成为人类世界中的上帝,还需要人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予以配合。换言之,在客观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受物及其关系的统治;在主观上,还需要人在意识中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关于前者,人类是通过物象化来完成的。所谓物象化是指“人格和人格之间的社会联系(die 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 der Personen)转变成一个物象和物象之间的社会关系(ein gesellschaftliche Verhalten der Sachen),人格的能力转化成一个物象的能力”。(Marx,1976/1981,S.9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物象化将带来两个后果:第一,在交换价值的制度下,由于人的活动及其社会联系无法表现为人格本身及其关系,而只能表现为人格之外的物象之间的关系,这会使人们之间真实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联系受到商品和货币等物的关系的遮蔽,致使人们无法发现物的关系背后的人的关系,从而产生下面的拜物教现象;第二,由于人格的能力及其社会联系都变为物的能力,这会使人格及其社会联系只有借助于人格领域之外的物象才能得到承认或者保证。于是,就出现了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主奴辩证法”相类似的情况:作为主人的人格因依赖于物的承认而变为奴隶;作为奴隶的物则因人格对自己的依赖而变成主人,人和物之间的主客关系发生了颠倒。关于后者,人类是通过“拜物教(Fetischismus)”来实现的。拜物教跟人的意识有关。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所述,所谓拜物教是指本来物(商品、货币)本身并不具有像神那样的魔力,它之所以具有魔力完全是由其背后人们之间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联系所赐,离开这些,货币只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和废纸而已;但是,由于物象化结构本身的必然性以及这一结构对真实原因的遮蔽,人们依靠日常意识根本就无法识破这一假象,反而将这一魔力“误认(Quid pro que)”为金银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反而向金银顶礼膜拜。(Vgl.Marx,1979,S.86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90页)结果,在现实中出现了商品拜物教或者货币拜物教等奇异现象,人类在精神上也甘愿跪倒在商品和货币的脚下,把商品和货币置于神坛。如果连人类意识也臣服于物,那么说物已经上升为世界的主体就再也无可争议。至此,我们分别阐述了人从主体地位失坠和货币上升为主体两个过程。在人与物的双重作用下,传统的“人与物=主体客体关系模式”终于解体。人与物互换了位置,物变为主体,人变为客体。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以物为主体的世界体系。如果非要模仿人类世界给这一新的世界体系中的因素,即货币、商品和人格排个序的话,在这一体系中,“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的存在,而商品代表货币的人间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3页)。金银这样的“物(Ding)”是上帝;商品这样的“物象(Sache)”是平民;而“人格(Person)”则变成了奴隶。如果说在人类世界上述要素是按照“Person→Sache→Ding”来排列的话,在物的世界这一序列则颠倒为“Ding→Sache→Person”。金银这样的物位于世界的顶端,而人格位于世界的底端。人格就像当初的物的遭遇那样,自己无法独立发挥作用,只有变成物的客体才有意义。活的劳动只有借助于死的物才能起死回生。虽然他们也以人的身份参与商品交易,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人格化的糖块”或者“人格化的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9页)。在“人与物=主体客体关系模式”下,人是物的所有者,而物是被所有者;但是现在连这一财产关系也发生了颠倒,物变成了所有者,人变成了被所有者。“我们自己的产品顽强地不服从我们自己,它似乎是我们的财产,但事实上我们是它的财产。我们自己被排斥于真正的财产之外,因为我们的财产排斥他人。”(马克思,第182页)令人震惊的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不幸,仍然热衷于相互欺骗和自由竞争,陶醉在打败竞争对手的快乐当中,孰不知,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人与人争斗的结果是物对人的全面的统治。古谚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意思是物没有人聪明,彼此相争而使人获利。但是,如今古谚变成了“渔翁相争,鹬蚌得利”,得利的竟然是那愚蠢的鹬蚌。如果说一个人被另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人所击败,还情有可原,但是人却被没有自我意识的、自己的创造物所击败,则无疑是滑稽可笑且令人难以接受的。故马克思戏称近代社会的这一尴尬事态为“类生活的讽刺画”(同上,第171页)。由物行使人在世界中的权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对经过了启蒙、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的人类而言,这无疑是一种侮辱。可能是为了强调这一事态的严重性,马克思与近代启蒙以来的思想传统相反,破天荒地将自己所处的时代,即人类社会的第二大发展形态定义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格的独立性”(Marx,1976/1981,S.9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阶段,把此前的原始共同体定义为“人格的依赖关系”阶段,把此后的未来社会定义为“自由个性”或者“联合起来的个人”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8页)。第二大阶段与其他两个阶段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物为主体,人对物的普遍依赖。当然,对马克思而言,第二大阶段属于人类发展的异化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它必将被扬弃。在未来的第三大阶段,“自由个性”将取代人对“物的依赖性”,人将重获主体地位,世界也重回人类世界。马克思虽然是在证明物必然对人取得胜利的逻辑,但是其目的绝不是让人类安于物象化和拜物教,停留在物的世界之中,他是要让人类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并从中找回希望。他写道:“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市民社会(die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Marx,1976/1981,S.9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9页)物的胜利是暂时的。随着货币转化为资本,物在发展到极致的同时也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这颗地雷将炸毁物的世界。总之,在经过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发展以后,物终于走完了它在《货币章》中的历程,进入了《资本章》。《资本章》是物的胜利逻辑的进一步深化和展开。在《资本章》中,资本取代货币成为世界的唯一主体,商品、货币之类的物则变为资本的配角。资本作为货币的更高次方,它要比货币厉害得多。它首先让劳动者及其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即让主体和客体彻底分离,让劳动者不是所有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然后,它不仅让人臣服于自己,而且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转化为自己增值的客观条件。自然界自不必说;人格以活劳动的形式变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或者“人格化的资本”;科学、技术、甚至民族国家、政治权利也成为资本的同谋或者帮凶,服从资本增值的目的。世界变成资本的世界。我们知道,从《大纲》开始马克思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共由“I资本→II土地所有制→III雇佣劳动→IV国家→V国际贸易→VI世界市场”六个部分组成。这一计划从“资本”开始,到“世界市场”结束。如果说前三个部分属于资本固有的内容范围的话,那么后三个部分即“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则属于资本向外部延伸、扩展的领域,它意味着资本将“国家”、“国际”和“世界”也都纳入自己的范畴,将人类文明变为资本的文明。这一安排在结构上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伦理篇”相似,黑格尔是按照“市民社会→国家(国内法)→国际法→世界历史”的顺序叙述的。他们的区别在于:黑格尔设定的运动主体是伦理理念;而马克思设定的运动主体是资本。《货币章》的主体是货币;《资本章》的主体是资本。人在整个《大纲》中从来就没有以主体的身份登场过。在这个意义上,《大纲》所呈现的是一个人不在场的理论世界。让人的世界中没有人!这正是马克思不同于近代启蒙主义者的地方,是他的思想独特性之所在。他是想以此来揭露资本主义的非人本质和证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但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特质和理论意图没有被很好地理解。一些西方学者以此为由来指责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说他彻底忽略了人,甚至以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倾向来贬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些学者试图替马克思辩护,将《大纲》解释成以人为主体的劳动逻辑,推测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中曾经存在的“雇佣劳动”分册应该有关于人的叙述。姑且不论《大纲》中的“活劳动”是不是就属于“雇佣劳动”分册的内容,即使有一天找到了那个所谓的“雇佣劳动”分册,其中的人也只能与《大纲》中的活劳动一样,只能是资本的客体条件。因为,让人以主体的身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出现是与他的物的胜利理论逻辑相悖的。最后,再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大纲》的物的胜利逻辑与《资本论》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同《大纲》一样,也基本上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资本”分册的实现。它虽然没有像《大纲》那样,采取《货币章》和《资本章》那样的两章结构,但是在叙述上,它也采取了商品→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的顺序,描述了作为物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以主体的身份征服世界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物的胜利逻辑也贯穿在《资本论》当中,在这一点上,《大纲》和《资本论》并无二致。但是,一些学者却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两者存在着差异。譬如,奈格里就提出,“《大纲》为了分析资本过程中的革命主体性,构建了主体性的路径”(奈格里,第27页);而《资本论》则以“客体化”为核心,缺少关于人的主体性路径的建构。为此,他还将自己的《大纲》解读著作命名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前一个马克思是指《资本论》,后一个马克思是指《大纲》,意思是《大纲》的理论水平高于《资本论》。可是,正像本文所分析的那样,无论是从文本事实还是从理论逻辑来看,奈格里的结论都是值得商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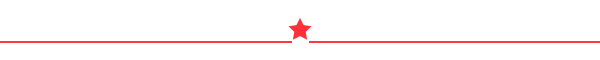
韩立新,2014年:《〈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黑格尔,1996年:《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马克思,2000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1998年,人民出版社。奈格里,2011年:《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Marx,K.,1976/1981,konomischeManuskripte1857/58,inMEGAII1.1,2,Berlin:DietzVerlag.1979,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 konomie,Bd.IinMEW23,Berlin:DietzVerlag.1981,AusJamesMill:élémentsd'économiepolitique,inMEGAIV-2,Berlin:DietzVerlag①“营利劳动”的原文为Erwerbsarbeit,人民出版社版将它译为“谋生的劳动”。笔者以为不妥,应译为“营利劳动”。
文献来源:《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